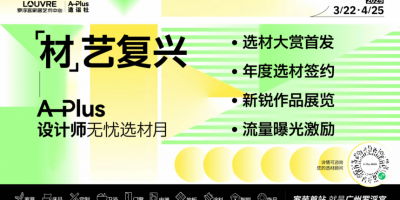新媒体艺术展策划人Timothy Druckery
记者:您是头一次来中国吗?对这里印象如何?
Timothy Druckery:我是第一次来中国,我很喜欢这里,喜欢它的独特气息。这个国家在飞速地发展,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存在,而新生的一代人又与传统的旧观念之间不断地发生碰撞。
记者:介绍一下您的教育背景和目前的工作吧。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展人,你自己也是新媒体艺术家吗?
Timothy Druckery:我在大学学习的是艺术史与摄影史。目前在马里兰学院担任摄影班的毕业指导。我从来都没当过艺术家。
记者:那么您是如何开始关注新媒体的?
Timothy Druckery:15年前恐怕还没有所谓的新媒体艺术这一说法。那时我住在纽约,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。我在纽约看到了很多展览以及音乐演出,来感受这里的艺术气氛。这个城市仿佛一个摇滚乐和实验音乐共存的大舞台,让我大开眼界。当时出现了一些以电脑、录像为主题的艺术作品,但是还不叫新媒体艺术。我在大学教授艺术史,觉得仅从这个学科自身角度看问题太过单一,所以我希望能从更综合的角度来看整个艺术的进程。于是我开始回顾整个二十世纪的媒体发展。我在研究电影的历史时,惊讶地发现在这个领域里独立与商业自始至终都是并存的。而整个二十世纪就像一个飞速转动的车轮,从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,充满着一连串的媒体爆炸。然而我也进一步发现在这个媒体的大环境里,传统艺术的历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。
记者:您如何看待“新媒体艺术”?
Timothy Druckery:我并不认同“新媒体艺术”这个词,因为“新”这个字眼太过工业化。我们通常都是在广告里听到“最新产品”、“最新科技”这样的说法。在工业化标准里,“新”就意味着更好、更快、更先进。但是旧的媒体从来就没有消亡,而且事实上90年代的很多科技在此之前都已经出现过了。互动的概念在80年代就已经有了,那时更多地是通过广播来实现的。有一些人专门建立无线电通讯网络来相互截获电波破译密码。然而直到第二代互联网出现时,一般的人还是不了解它其中的奥妙所在,人们并不理解科技的本质。而最早接受这些科技的人恰恰是艺术家,是他们对这些技术进行了最早的应用和试验。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科技,他们知道如何去操作各种工具。然而媒体艺术家们则致力于发现那些没有被实施过的操作,不断地挖掘可能性。
记者:您如何看科技对社会的影响?
Timothy Druckery:这个社会的文化在慢慢转变为一种“屏幕文化”,人们日常接触的都是“屏幕媒体”,因为他们越来越习惯看屏幕了。法国一位哲学家有一句名言:人们之间的交流已经全部变成图像之间的交流了。作为搞摄影出身的我也深有体会,过去人们摄影都是通过照相机上的取景器来观察,而现在他们只用看液晶屏幕了。从“取景器”(Finder)到“屏幕”(Screen)的转变就能看出观念的变化。当人们通过“取景器”观察时他们是在“选取”真实的世界里的“景”,而当他们通过“屏幕”观察时他们看到的则是一堆图像。这些图像和真实之间是不对等的,人们观察的角度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。我在中国的餐馆点菜时,虽然看不懂菜名,但是通过图片也能够进行选择。我只要像按鼠标一样“点”一下图片,服务员就会把菜送上来。你会发现所有的语言和文化理论都在这一瞬间变得毫无用处,因为图片把所有的复杂性都给消除了。这是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,值得人们好好反思。以前人们是在记录这个世界,而二战之后,人们开始“渲染” 这个世界。这样一来我们如何理解世界?早在九十年代初人们就已经能拍出《侏罗纪公园》这样的电影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不一定是真实的,它可能被电脑处理过,就连报纸上的新闻都不一定是真的。人们不禁会问:这一切发生过吗?信息的可靠度发生了变化,这正是电脑带来的灾难。
记者:您认为媒体技术在未来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?
Timothy Druckery:我不知道,科技的发展太迅速以致难以预测。不过目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,高清的普及使我们有机会享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画面分辨率,而人们却执迷于用分辨率最低的工具来观看图像,比如手机。当然不管怎么说科技的影响依然很强大。有人宣称摄影已在数码时代消亡,但是现在人人都有数码相机,你又怎么能说摄影消亡了呢?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变得高度的电脑化,他们一出生下来就会接触到电脑,并会与之相处一世。也许他们不会再追问萦绕我们这代人的那些问题了。
记者:您觉得媒体艺术家在当下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?
Timothy Druckery:艺术家应该从历史的回顾中寻找根源。例如互联网的概念,其实就来源于过去的邮件系统。艺术家应该去思索如何理解被遗忘的东西。艺术总是在提醒人们什么东西在历史进程中遭受了失败,而电视这样的大众娱乐则恰好是它的反面。艺术家们不应该直接利用电脑,而是要打破和分解它,从更内在的角度来说清事物的原本。